24 / 05 / 13
隨筆|歷史的弔詭之處——普魯士軍官團是一戰的罪魁禍首嗎?
普遍被人們接受的一戰罪魁禍首是德國軍隊,尤其是普魯士的軍官團。但是如果仔細研究一戰前軍備競賽的情況,其實會發現一個很弔詭的地方,以普魯士軍官團為主的陸軍恰恰不支持軍備競賽。一戰前英德交惡的大致脈絡是這樣的,德皇拍拍腦袋決定要讓德國成為世界強國,而一個世界強國就必須配備有世界強國的海軍,於是他老人家就支持建造海軍。而海軍的霸權恰好是英國人的命根子,德國人這麼幹就是戳到了英國人的肺管子上,所以兩國就從一開始的好哥們,逐漸相互看不順眼了。
我們來分析分析,為什麼德國人想要建立海軍呢?海軍有這麽幾個好處:
-
德皇他老人家比較喜歡
-
可以為中產階級以及非普魯士的德意志邦國提供上升空間
-
為工業家創造更多的訂單
這第一點看起來比較好理解,但是後面就不是那麼容易理解了。工業家支持新訂單或許不難理解,但是為什麼軍備競賽沒有招致普通民眾的反感,反而獲得他們的贊同呢?這是因為德意志帝國的國家結構是以普魯士為主的,普魯士又是由保守的容克地主佔據主導地位。容克地主們把持了普魯士陸軍,所以陸軍是一個貴族程度很高的部門,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普通民眾並插不進來。不僅僅是普通民眾,像是巴伐利亞這些非普魯士的邦國也插不進來。沒有辦法把觸角伸進核心部門,就沒有辦法獲得權力,沒有辦法獲得權力就沒有辦法獲得利益。
所以當有人提出要擴建海軍的時候,他們看到的首先不是軍備競賽,而是一個擴張自己權力的好機會。企業家們可以獲得更多訂單,工人有了新的就業崗位,社會民主黨獲得了更多的議會席位(這裡順便說一下,帝國越製造這種嚴重依賴現代化工業的戰艦,工人的力量就越強,比如說,一戰時期的俄國後期政治權力很大程度上就落在了國防工業委員會的頭上);中產階級終於有了參加軍隊揚眉吐氣的機會(成為一個軍官那個時候是成功人士的象徵);帝國內部的其他邦國也能在重要問題上說得上話。
除此以外,傳統的普魯士貴族對於民族主義這種意識型態是比較抵制的。如果我是一個貴族,我首先是xxx領地的貴族,xxx領地的臣民是我的屬民,這並不與他們的種族成分有什麼關係。他們很少會想到自己首先是一個德意志人,其次才是一個xxx地的貴族,德意志作為一個民族的概念對老一輩人來說是一個陌生概念,甚至是一個激進的概念因此惹人反感。舉例來說,本來我是xxx領地的貴族,我只需要管好我這一畝三分地的事就好了。巴伐利亞和法國打成一團關我一個普魯士人什麼事呢?我就喝茶看報發展我的莊園就好了,並不需要牽扯到我領地之外太遙遠的地方。但是假如我變成了所謂的德意志人,那麼法國人吞併巴伐利亞就變成了法國人侵略德意志民族了,我雖然是一個普魯士貴族(順便說一句,普魯士人也不是德意志人,如果硬要從血統上來說,應該是斯拉夫人,不過血統從來不重要,民族一直都是一個政治和文化概念),但是為了德意志民族的榮耀我也不能坐視不管,於是我就動用了我自己的財產去巴伐利亞抵抗侵略。這樣的戰爭仗打完了,我雖然什麼也撈不著,但是我捍衛了德意志民族的榮譽。
這種新穎的觀點在傳統貴族看來就是吃飽了撐的,完全是賠本賺吆喝。但是對於帝國境內大部分非貴族來說並不是這樣。他們本來的身分僅僅是xxx地的臣民,但是如果接受了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他們馬上就具有了和貴族老爺們共同的身分。原來我是xxxx爵爺治下的臣民,現在我和爵爺一樣都是德意志民族的一份子,在這一點上我們都是平等的。甚至因為我是只會講德語,而且也沒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外國親戚,我比爵爺還要德意志一些。
德皇(他老人家德意志民族主義中毒頗深,覺得自己可以代表整個德意志民族,並且認為德意志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天命必須要由自己來完成)提出世界強國的戰略,以及擴建海軍也正好滿足了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這種意識型態。統一的、抽象的德意志越強,封建的、擁有具體權利的貴族階級就越弱,這是一個人民戰勝貴族的好機會。這是另外一個原因為什麼普魯士貴族要抵制海軍建設。
如果我們舉行一次民主投票,大致統計一下結果,結果可能大概是這樣的,絕大多數的企業家、中產階級支持皇帝的世界強國策略,支持增稅,支持軍備競賽,仇恨英國佬和法國佬(這當然也是民族主義的一個具體表現了);相反,普魯士貴族們卻不支持擴建海軍,不支持增稅,同樣地,也不會仇恨他們的英國貴族親戚們。
但這也正是歷史的弔詭之處,一戰結束之後,人們一致認為普魯士軍官團要為戰爭負責。相反,普通民眾和中產階級們只不過是被這些腐朽的好戰份子綁架了,他們本身並不是有罪的,只不過是被誤導了而已。我們當然不能說普魯士貴族完全沒有責任,但是他們至少並不應當承擔主要責任。中產階級們當然不是無辜的,但是歷史的書寫掌握在他們的手裡,只要過個幾百年,人們的認知就會完全被扭曲了。
除此以外,另一個值得學習的地方又牽涉到了我之前說的名實之分。我們現代人想當然的使用德國人、德意志人來理解這段歷史,但是這個概念其實模糊不清,而且可能包含了兩個此消彼長的勢力團體。貴族和臣民都被我們認為是德意志人,但是人民權力的上升要求貴族地位的下降,兩者之間其實並不是和諧融洽的關係,所以當我們用一個概念去理解兩個相互矛盾的現實時就會陷入認知的偏差。
在我們閱讀歷史,甚至分析現實的時候,我們也要儘量避免名不副實帶來的認知迷霧,那些看似是一回事的東西其實並不一定是一回事。如果統治者並不誕生於被統治者的階級,換句話說,如果某個國家的人民並不是自治的,而是被治理的,那麼這就一定存在著兩個不同的權力結構,他們之間無論多麼相像,擁有這相同的名頭,語言和文字,但是他們仍然不是一回事。比如說,薩達姆統治時期的伊拉克,權力掌握在遜尼派手裡,但是大部分人口卻是什葉派。雖然他們具有這相同的名字,伊拉克人,說著相同的語言,具有相同的風俗和生活習慣,但在現實中,他們仍然是兩個水火不容的團體。一個什葉派伊拉克人,因為伊拉克人這個名頭,對現實產生了名不副實的認識偏差,選擇了為遜尼派的統治者赴湯蹈火,甚至因為家裡人沒有為伊拉克民族著想,不惜犧牲他們自己人的利益。
假如我們具有上帝視角看著他的所作所為會不會覺得讓人笑掉大牙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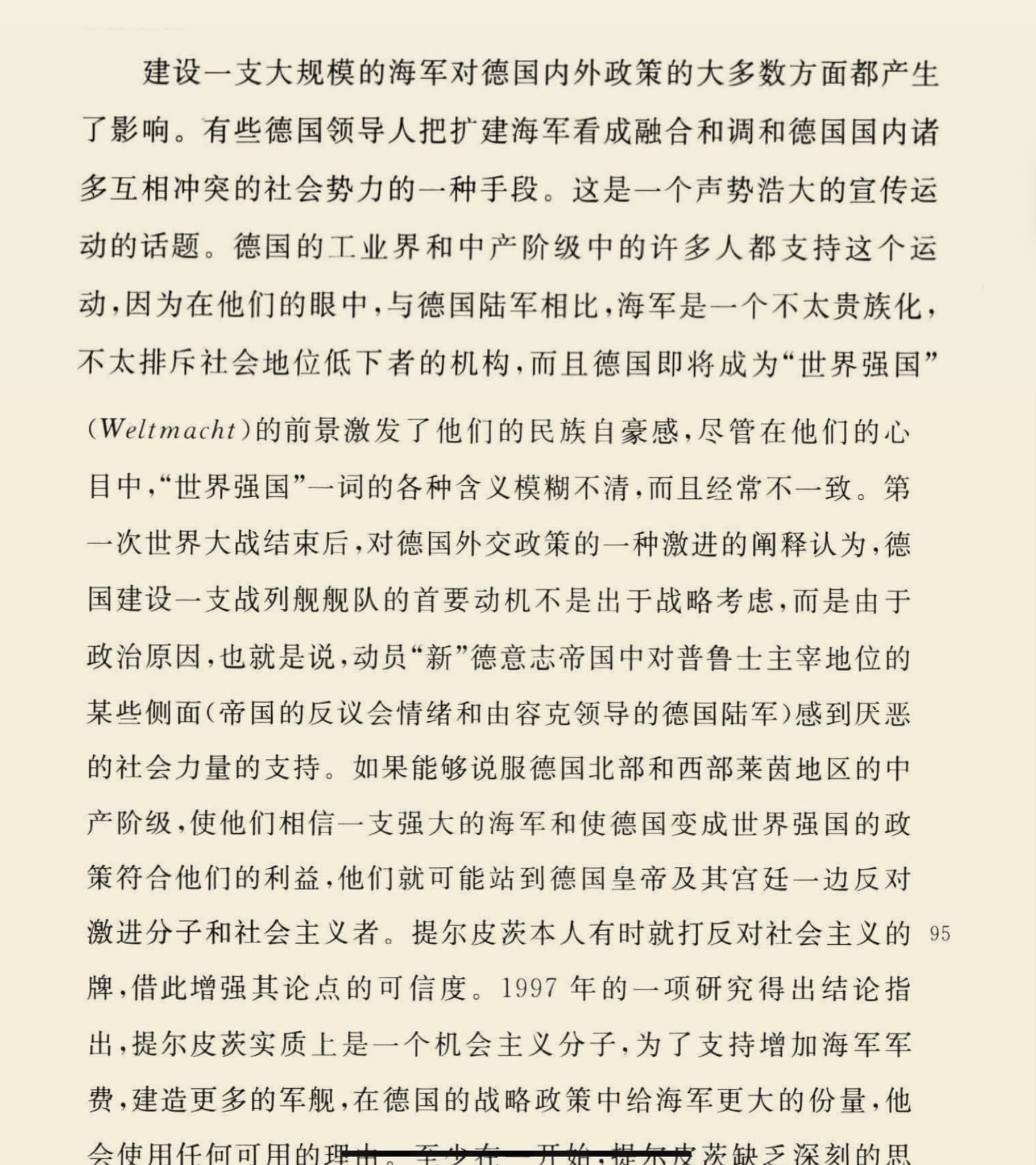
#名副其實與名不副實